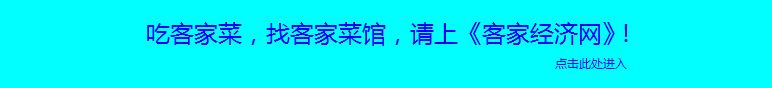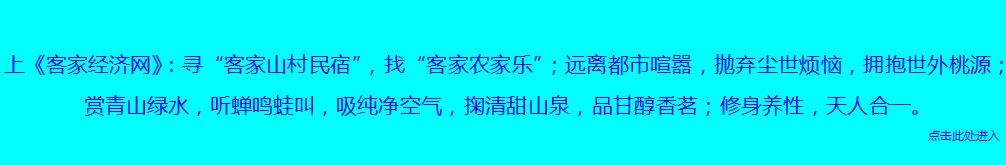| 客商研究 |
| 客家商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 客家商人的爱国爱乡观念与行为 | 客家商人的经营管理之道 | 客家商人失败案例 | 与客家商人有关的法律案例 | 客家商人的家庭教育、二代与后代 | 客商与潮商、广府商人、闽南商人、苏商、浙商、鲁商、徽商、晋商的比较研究 | 客家商人研究综述 |
| “客 商”论 |
|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9 月 15 日 0 时 37 分 2 秒 来源: 嘉应学院财经系 谢友祥1, 闫恩虎2 2004-3-1 0:53:31 |
|
摘 要:“客商”作为广东历史上的“四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商帮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积极的人文影响。“客商”所具有的“儒商”特质、崇名务实的经营之道,以及超常的社会亲和力,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有人文借鉴意义。同时,作为当今“华商”网络的重要一员,“客商”对于促进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以及构建统一贸易区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客商文化”对于新时期我国的商业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客商”;“儒商”;崇名务实;社会亲和力;现实意义 一 自西汉以来2000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统治权力被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商人的生存和发展只能靠同官员建立一种隐秘的权力——利益交换网络来维持,而这种维系网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或乡亲或宗亲。由于当时交通、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制约,地域关系成为比较可靠的联系纽带。因此,以乡亲为纽带的封建“商帮”产生了。“商帮”以地域为聚结点凝成网络,依靠各种内部隐秘关系从封建朝廷中取得某种国家专卖品(诸如食盐、铁、煤、粮食等的市场经营权以及某些战备品的生产和供应权,以此谋取群体利益。对朝廷及官员,他们要进贡和行贿;对地方势力,他们要笼络和勾结;对市场,他们要想方设法挤走竞争者取得垄断权;对内,他们要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在这种环境制约下,“商帮”便逐渐成为具有内部组织和行业管理的社会势力。特别是明清朝廷颁布禁海令以后,“商帮”的海外贸易便带有走私的性质,他们必须和官员建立更加隐秘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内贸也一样,由于没有商业流通的法律规范,不仅各种苛捐杂税难以应付,而且其财产随时可能被抄收。商业听任于政府官员的随意操作,尤其是跨区域贸易,商人必须以一定团体同官员建立长期关系才能保证其商业行为的可续性,这样,商帮组织便逐渐严密化和程式化。明清时期,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晋帮”、“临清帮”、“徽帮”、“江右帮”、“洞庭帮”、“龙游帮”、“宁波帮”、“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十大“商帮”之外,广东的“客家帮”和“海南帮”也是比较著名的商人集团。这些“商帮”以地域为纽带,或合而与朝廷取得联系,或协调与其他商帮争斗;在海外贸易中,则既要防朝廷缉查也防海盗,又要联合防止土著的侵袭。斗争发展的需要,使他们逐渐形成有一定“涉黑”性质的团体。“商帮”组织以“会馆”为据点。所谓“会馆”就是中国的“商帮”势力在某个地区进行活动,为谋求商业利润与商业秩序而组织的网络。现在海外的各种地方会馆便是当年“商帮”组织的延续。当时,不同“商帮”经营不同商品,拥有不同的线路和市场范围,也有着不同的经商理念和社会态度,形成中国历史上各具特色的“商帮文化”。 “客商”作为广东四大“商帮”之一,尚未列入中国十大“商帮”之中,说明其在当时商界的影响并不大。这与“客商”的形成渊源和从商理念有关。但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纵观“客商”的形成发展史,就会发现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有着其他“商帮”所没有的文化特质。可以说,“客商”之路,不是简单的经商谋生之路,而是开拓和平之路,是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历史传承。 二 所谓“客商”,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从商的客家人,二是“客家商帮”的简称。前者比较宽泛,而后者则是一种特指。由于“客家帮”是中国传统“商帮”中内部组织最为松散的,许多客籍商人在从商经营中甚至没有过“结帮”的经历。可以说“客家商帮”是一个文化内涵大于组织形式的概念。虽然海外许多地方都有各地客籍会馆,但其联络功能远大于其帮派功能,因此,“客商”是一个比较宽泛且理念性较浓的概念。要讲“客商”,必须先讲“客家”。客家先民原本是中原人,多为贵族后裔,东晋以后为避战乱南迁。现在主要聚居在闽南(?)和粤东。“客商”大概形成于明中期以后,成熟于清康乾以后。根据地域特色,“客商”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闽南“客商”,从漳州出海,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做生意,代表人物是胡文虎;二是粤东“客商”,从汕头出海,到东南亚,代表人物是张弼士。由于本文论及的是广东“客家帮”,故论述主要指粤东“客商”。 “客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客商”多为外拓商,即多从事海外开拓,主要是在东南亚诸国。而且从业经营的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易,而是带有开发性质。这是因为“客商”形成于明清中期,这时国内市场已被其它“商帮”分据,他们已无法涉足。另外,客家人的处世之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崇尚“读书致明”,作生意是不得已,带有被迫性质,是为了谋生。而当时的南洋开发,是明清中国“四大移民潮”之一,许多没法读书或读书未仕者使乘此潮出海,去南洋谋生开拓家业,形成“客商”。第二,“客商”多是创业商。因为客家人的文化情怀,较少形成专业的商人家族,开始做生意是迫不得已,成功以后,有的回国捐官,有的留在当地做统领或豪绅,其子女多半去读书或当头领,绝少有继续从商的。第三,“客商”多为“奇缘商”,因为他们初次经商,一没资本,二没有组织,三无经验。白手起家,一靠机遇,二靠智慧。因此,“客商”巨富大多具有传奇经历。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大埔人)开始在印尼的鱼档打小工,因为他建议老板将富余的鱼制成鱼干,结果老板获利,他也从此步入商界。因此,我们研究“客商”,重在他们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而不是重在其商业之道。 三 “客商”纵横东南亚,大约有三四百年,他们不仅将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社会文化带到当地,推动南洋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艰难的从商开发生涯中,由于独特的生存背景和文化传承,形成他们独具特色的从商理念和经营特点,这就是“客商文化”。 第一,“客商”有着独特的“儒商”情怀。“在商言商”,而“客商”却是“言商向儒”。因为,客家人从商是被迫的,客家先民是中原贵胄后裔,读书致仕是他们治家立业的首要愿望。这一条路走不下去才考虑经商,客家人将出海经商称之为“过番”,是谋生求存不得己而为之。这同“晋商”恰恰相反,“晋商”传统是“学而优则贾”,“晋商”也重视读书,但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生意,所以,“晋商”家传的谚语是“生子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而客家民谚是:“读书(赚的)钱,代代钱;生意钱,日日钱。”“客商”从商带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既有着儒家的“正途”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商儒不双兼”,但又必须面对现实,求生存。这一点也不同于徽商的“易儒而商”或“易商而儒”。“徽商”是主张“儒”“商”两行的,所谓“无徽不商”。出身于“徽商”重门又为大儒的汪道昆说:“余唯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这就是说,“客商”大都是带着儒家情怀去经商的,他们是求儒不得进仕而被迫从商。因此,“客商”成功后,大多从政,或投资文化产业,以圆其从文致仕之梦。而且“客商”带回家的钱大多用于公益文化事业。其实这正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一种体现。因此,可以说“客商”大多都有一种儒家的济世情怀,是经典的“儒商”。中国封建时代能够致富的商人,一是皇商,依靠给皇家采购物资致富,像后期晋商;二是依靠官府背景获得行业垄断利润的商人,如“徽商”中的“盐帮”和广东十三行行商等。而“客商”多为创业商,张弼士是从小鱼贩起家,叶德来(1837—1885,广东惠阳人)是小伙计出身,姚德胜(1859—1915,广东平远人)小贩出身,他们出身贫寒,白手起家,靠的是智慧和诚信。“客商”成功多靠人格魅力,标榜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没有欺行霸市的公开记录,这正是“儒商”的根本体现。 第二,“客商”奉行崇名务实的经营之道。崇名务实是客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在“客商”的经营之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客商”文化的一个独特内容。虽然大多数“客商”未必都能做到“名”“实”相符,但“崇名”是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受文化底蕴的深刻影响;“务实”是他们行为的客观表现,是因为生存艰难使他们养成这样的行事风格。“崇名”既包括“正名”,也包括“名分”。“正名”之道,是儒家处世的重要内容,“客商”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很深,迫于生存被迫从商,骨子里仍存有“蔑商”意识,这就使他们在经营中尽量使其行为向儒家的理念上靠,尽量避免在世人眼中滑入“奸商”之列,最基本的是在经营中坚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人气旺,财气兴。”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地方的事务管理,参与捐资兴建公益事业,有一定积蓄就谋取各种荣誉和名号,以此证明自己虽“从商”但仍属“正道”。元初、明初以及清初的中央政府,严格实施禁止民间商人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但活跃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帮”、“潮州帮”和“广府帮”等海商集团为了谋求高额利润,突破“海禁”封锁,在东南沿海从事贩运和走私。虽然“客商”的居住地同样靠近沿海地区,却没有从事这些对抗朝廷的贸易,也没有形成与朝廷或当地土著抗衡的武装势力,而且也从没有形成强大的组织,“客家帮”只有一个松散的联系点,即各地的客家会馆,进行联络或处理一些乡亲关系,而会馆的组织和领导者,也不一定财大气粗,多半选以德、义著称的长者。“崇名”意识使“客商”们非常注意“利”和“义”的关系,他们多追求“义”“利”并举,反对见“利”忘“义”。另外,客家民系的家族对“名”特别重视,这就使“客商”的行为受到文化和家族势力的双重制约。至今,“客商”们留下的深宅大院中到处壁刻有儒家经典和处世礼义对联。崇名的另一方面,是对“名分”的重视,“客商”较少一生单纯为商的,多半成功后捐资谋官(从政),或投资文化事业(立言),或修桥铺路作慈善事业(立德)。“务实”是“客商”经营之道的重要特点,他们多半是白手起家创业的,只有努力勤俭才可能成功,他们没有冒险的资本,只能靠精打细算,从小做大,这种经历使他们成功以后仍保持这种处世风格,因为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讲求花一分钱要有一分钱的效用,缺乏大的气魄。这也是“客商”中较少出大商巨贾的原因,也许正因此“客商”未入中国十大“商帮”之列。“客商”中的典型代表张弼士,印尼经商成功后,费心思回国担任清廷粤汉铁路、佛山铁路帮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戴三品顶戴。在慈禧避难时他捐赠3万两白银,孙中山闹革命他也捐3万两白银。还有姚德胜,光绪年间,他捐6万银元救灾,光绪帝特赐“乐善好施”匾,并诰授四代二品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孙中山闹革命,他也捐巨资赞助,并获孙中山颁发的“一等嘉禾勋章”。在多舛乱世,这也算是“名”“实”俱保的最高境界了。 第三,“客商”具有超强的社会亲和力。“客商”在文化上具有强势,他们到海外经商,不谋求集团的强势欺压,和当地土著亲和,这本是客家先民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养成的良好品质,在“客商”的经营中也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他们不谋取暴利,而且赚的钱也不是全部汇回老家,而是用大部分钱参与当地的开发建设,大多数“客商”都娶当地土著为妻,繁衍共荣。姚德胜曾在马来西亚重建怡保;张弼士曾被西方殖民者委为领主治理区域;叶德来曾被当地马来人拥为巴生和吉隆坡两地甲必丹职务,后被委任为吉隆坡地区行政首脑。在以后20多年间,叶德来以极大的毅力和过人的才能,把贫穷落后不足千人的吉隆坡,建设成为马来西亚早期繁荣发达的大埠,被誉为“开辟吉隆坡的功臣”;张榕轩(1851—1911,广东梅县人)、张耀轩(1861—1921)两兄弟,也曾被任命为印尼的“甲必丹”和“雷珍兰”,主持地方政务。现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许多政要和名流都是“客商”后裔,其中有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菲律宾原总统阿基诺夫人,圭亚那原总统阿瑟•钟等。“客商”经商处处考虑当地利益,讲求“利”“义”并举,弘扬的是儒家“仁道”,不进行掠夺性开发或掠夺性经营。更可贵的是,“客商”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地方首脑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强势移民,而是尊重当地人。 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客商”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内涵,但它作为一种现象和商业文化对我们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已逐渐联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网络。但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由发达国家推动的,这些发达国家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年殖民宗主国的思维定式,以推动全球化为名目,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变相掠夺和经济干扰,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制造许多难题。同时,发达国家将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今天,我们研究“客商”的文化情怀和社会亲和力,也是给某些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以启示,要尊重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权益,要和谐以求共同发展,不能进行强势经济掠夺;人类不要分贫贱和种族,要互相尊重,这样才能建设好一个祥和的“地球村”。这样,各国及其商业集团才能有祥和的市场基础,各种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也才能从源头上得到遏制。 第二,“商帮”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在国内消失,但散布海外的粤闽“商帮”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形成复杂的“华商”网络。“客商”作为现在“华商”网络的重要一员,在东南亚各国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很多是国际商界的知名人士。利用“客商”网络,促进我国和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对改善我国目前的外贸体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利用“客商”网络沟通,推动东太平洋统一贸易区建立,对提高我国经济辐射有相当现实的作用。而且,利用“客商”网络,对于内地欠发达“侨乡”的招商引资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客商”文化中的“儒商”情怀对于我们今天整顿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利义并举”、和睦共处、不欺行霸市、富贵不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客商”文化中的精华,对于新时期的商业道德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打击假冒伪劣、走私贩运等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03) |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