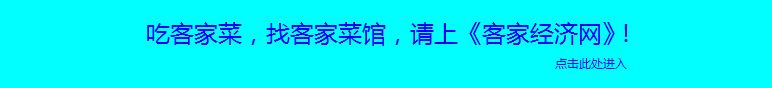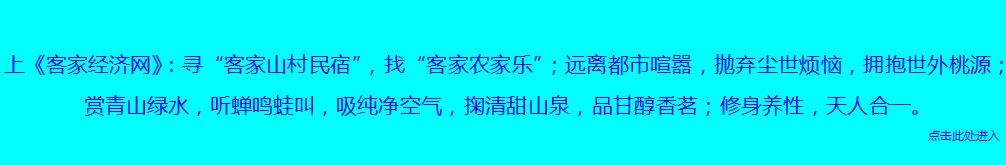| 客家文化概要 |
| 客家文化综述 | 客家认同 | 客家精神 | 客家话 | 客家文化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报刊杂志、专著 |
| 族群的认同与重构——以客家为例(上) |
|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2 月 15 日 12 时 51 分 10 秒 来源: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赖广昌 2006-6-22 13:51:25 |
|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第二节 已有研究的回顾 (二)目前国内关于族群研究的进程 第二章 研究的问题、设想、方法 第三章 客家族群认同与重构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之实证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