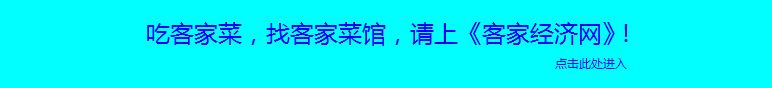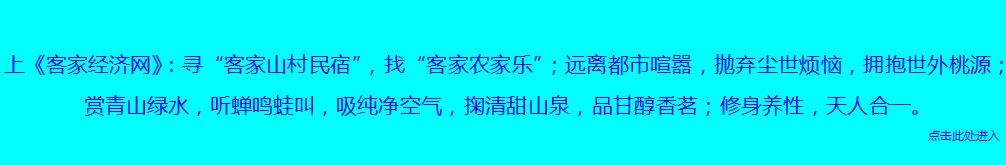| 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最新比较 |
|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4 日 14 时 3 分 56 秒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冯兴元 2001-9-12 10:34:22 |
|
按:今年以来, 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出现了融合之势。苏南学了浙江的股份制,浙江的私企则有不少走向联合。在两种模式趋同化的背后,是活跃的江浙经济在不断寻求适合自己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核心的变化就在于产权制度的变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