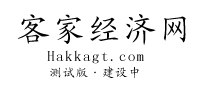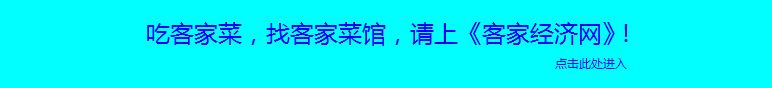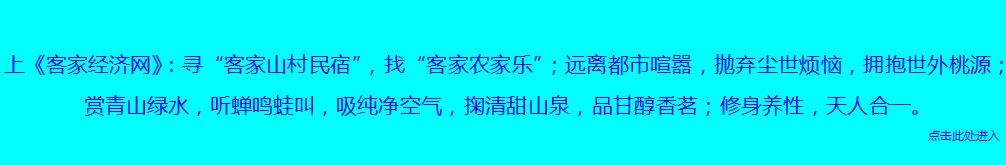| 吴佑寿:峥嵘岁月清华园 |
|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4 月 8 日 22 时 32 分 51 秒 来源: 中国科学院网站 来源:《科学新闻》2009年第18期 2009-9-30 22:54:41 |
|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 记者从吴佑寿院士家中采访出来,漫步在清华大学荷清园小区的林荫小道上,回想着吴佑寿先生那血肉丰满的历史回忆,耳畔不由依稀响起清华老校歌恢弘的旋律。恍惚中,感觉又回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饱经风雨却巍然屹立的清华园。 “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 作为海外华侨,吴佑寿1938年在曼谷中华中学读初二。然而,由于泰国的排华政策,包括中华中学在内的所有华文学校全被关闭,吴佑寿携弟弟吴佑福离泰赴港继续学业。1941年,香港沦陷,他又带着弟弟返回内地。1943年,吴佑寿毕业于广东梅县梅州中学,同年入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在学一年,因志趣不合,对重庆政府贪污腐败、消极抗日尤为不满。在家庭经济资助断绝的情况下,他毅然转学,在华侨同学罗振铣的帮助下辗转周折,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 抗战胜利后,清华师生北上返校不久,1946年12月发生的北大沈崇事件引发了“抗暴”学生运动。吴佑寿告诉《科学新闻》,“抗暴”等一系列学生运动让青年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切身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不可救药。与此同时,包括《冀东行》在内的一些介绍解放区民主生活的小册子也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让青年学生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当时,清华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进步活动,“一二一”图书馆、读书会、“大家唱”歌咏队、剧艺社、美术社等,使学生们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吴佑寿和他的夫人——生物系1946级的李佩环,就是在读书会上相识、相知、相爱、携手到老的。 对于当时清华园的进步氛围,吴佑寿对《科学新闻》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切希望,很多毕业的、甚至还未毕业的同学都积极争取去解放区。他回忆,当时班上的何芹田和吴开文是地下党,班上的同学想去解放区都通过他们俩联系。面对着同学们报名去解放区的澎湃热情,何芹田对大家说,解放区是很好,也很需要人,解放区的革命之火是熊熊大火。但是,同样也需要有人继续留在蒋管区,让蒋管区的星星之火也热烈燃烧起来。在清华园,同学们一样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回忆起当年参加学生运动,吴佑寿说,1948年7月9日,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血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沿着铁路步行进城去参加游行。到西直门时,城门早已关闭,国民党军警不让游行队伍通过,埋伏在京包铁路沿线的国民党特务捡起铁路上的铺路石袭击学生,手无寸铁的清华学生只能挥舞手中的标语牌挡避凶猛、尖利的石头,不少学生因此流血负伤。学生们一直坚持到晚上才返回清华。返校途中要经过一百多米长的海淀街,这是漫漫田野中通往清华园的唯一大路,但是,当地反动民团挡住路口,不让学生队伍通过。当时大雨滂沱,学生们被淋得湿透,直到午夜才被放行。我们回到明斋食堂,留校同学和食堂师傅已为我们烧好姜汤,令人感动。 在解放战争和清华解放的过程中,清华地下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师生先后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清华园被人们喻为“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 最后的疯狂 1948年7月,在镇压东北学生的“七五”血案发生后不久,清华大学社会系1947级的徐芳伟(古进)带上刚在沙滩北大北楼出版的快报,打算到东北同学的住处去。才行至沙滩后街西口,被封锁包围北大的警察拦住检查,将支持东北同学宣言的快报没收,徐芳伟也被带走,关押在草岚子胡同13号“北平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在徐芳伟被捕期间,吴佑寿与梁时熹以梅州中学校友的名义多次到监狱去探望。徐在特刑庭上坚贞不屈,机智应对,经历了1个多月的狱中斗争,于8月24日由清华大学出面请老校友、光华木材厂的老板担保出狱,后于10月经天津奔赴解放区。 机械系1946级的徐应潮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八一九”事件。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大批军警冲进清华园,按照“黑名单”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由于地下党的精心掩护,清华没有一个上“黑名单”的同学被搜捕到。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躲避,由于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事后,梅贻琦校长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的首次。” “八一九”当日,罗伯特·温德教授把剧艺社成员傅 藏在他卧室里的一个大衣柜里并上了锁。特务进屋要他开锁时,温德教授推说钥匙丢了,才躲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查。第二天,王珉代表组织通知徐应潮,认为包围清华园的国民党军警很可能再次进校搜捕进步学生, 让徐应潮当天半夜护送傅 和另一位“黑名单”上的进步同学林方其去解放区。 8月20日午夜,徐应潮等三人翻墙出了清华园,在月色中刚穿过茂密的高粱地,就被埋伏在高粱地里的国民党特务堵住,押送到德胜门的看守所。徐应潮后来又被转押至特种刑事法庭监狱,最后因特刑庭“证据不足”,由学校出面保释后立即前往解放区。而先于他们一天被捕的李詠和张家炽则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出狱。 吴佑寿向《科学新闻》讲述了一件他的同学去解放区的趣事。 1948年“八一九”前夕,几个同学相聚在西直门附近的何芹田家,为要去解放区的朱平洋、杨远馨(罗甫)、郭其佺三位同学送行,因为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当天晚上都回不了学校。他们穿上老百姓的服装,摘下近视眼镜,约好在天津南站碰头,再乘火车到泊镇,一同去解放区。由于白色恐怖,他们三人彼此不能打招呼,只能单独行动。在火车站,朱平洋、杨远馨看到同批去解放区的三个人都到了,各自安心上了火车,而郭其佺却因为深度近视,没看到朱、杨两位,他以为情况有变,就没上火车。出于安全考虑,他也没返校,直接在校外找地方隐蔽起来。朱平洋和杨远馨到解放区后,却发现郭其佺没来,担心郭出事,赶紧发信告知吴佑寿,吴佑寿将情况通知何芹田,通过地下组织终于找到郭其佺。后来,吴佑寿又帮郭其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郭其佺再次向解放区进发。这一次,他顺利地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 初露曙光 1948年12月13日拂晓,解放军进军至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的平川地带,遇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在得知前方即圆明园、清华大学后,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大学等古迹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 12月15日凌晨2时,毛泽东亲笔批示关于《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的军委通知。12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2月18日,第13兵团政治部在清华西校门张贴布告,全文是:“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布告,俾众周知!”落款是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当天晚上,前线部队两名干部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的家中,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此事令梁思成深深感到共产党对保护古迹的重视,激动不已。 1949年1月4日,清华大学张奚若、费孝通、李广田、钱伟长等37名教授与部分燕京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清华、燕京二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吴佑寿告诉《科学新闻》,1949年前后,离开清华的教师极少,相反,从南方、海外回来的教师却很多。当时,吴晗、钱伟长力劝大家不要走,章名涛教授从上海回来,钟士模、常迵从美国回来。梅贻琦校长处在他的位置上不得不走,于12月21日从东单广场乘飞机离开了北平。此外,仅有外语系个别教师离开了清华,其余的269位教师全部留在清华园等待解放。 “清华园解放后,维持清华原学制,教学照常。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课程设置学习前苏联,才将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吴佑寿说。 “永远的校长” 在清华园,真正称得上缔造传统的校长,当推梅贻琦和蒋南翔。 谈到梅校长,吴佑寿由衷地说:“梅贻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清晰,知人善任,很能团结人。在西南联大时期,也是梅贻琦主持联大的日常校务。提起梅校长,大家都很尊敬。”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梅贻琦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47名学生之一。在之后的岁月里,梅贻琦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代表了这位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对于清华园的殷切之情。 自清华建校以来,校长走马换将,更迭频繁,直至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清华大学的管理才开始稳定。 梅贻琦倡导通才教育。他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作基本训练。 对于现在一些人对蒋南翔在校长任上给清华大学赋予了过重的政治色彩颇有微词,吴佑寿认为,对于清华,蒋南翔校长是有大功的;对于我国教育,他也是有贡献的。 吴佑寿说,对于清华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惨遭“肢解”的遭遇,当时蒋南翔校长深为痛惜,他说:“清华是大泻肚子了。”院系调整后,蒋南翔校长为清华大学的多科性学科布局倾注了心血。1952年,蒋校长不顾前苏联专家的反对意见,在电机系电讯组的基础上建立无线电工程系。1956年后,又陆续设立了工程物理、计算机、自动控制以及电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和无线电物理等基础专业,理工结合,不奉行“以设备为纲”的实用主义。 “外面要求清华做这做那,我能挡就挡,让你们能够在学校里安心教学,同学们能安心学习”。回忆起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动荡岁月里,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小范围干部会议上说的这句话,吴佑寿仍然感动非常:“这是我亲耳听到蒋校长说的。” 事实上,蒋南翔就是这么做的。对于当年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运动,蒋南翔总是让清华“尽量慢半拍,能拖就拖,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清华的干扰”。 正因为在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的这种氛围,在十年动乱中,有人将清华称为“不漏气的发动机”。 |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