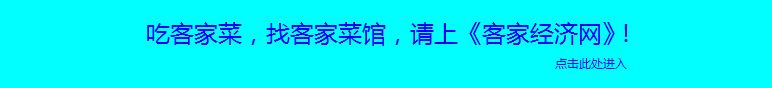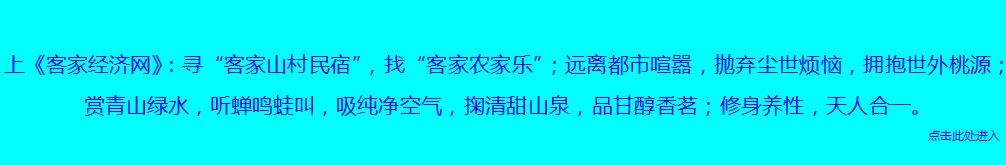| 站内搜索: |
| 客家企业家 客家亿万富豪 |
| 家居家具制造业 | 家居家具零售业 | 木竹业 | 纸浆造纸及纸制品业 | 印刷包装业 | 医药和保健品业 医疗器械业 | 日用化工业 | 化工业 | 橡胶塑料业 | 玻璃与陶瓷业 | 酿酒业 | 食品饮料业 | 现代产业化农业与观光农业 | 饲料业 | 能源与节能业 | 旅游酒店娱乐业 | 酒店设备及用品业 | 饮食业 | 汽车制造业 | 汽车零售业 | 汽车零部件业 | 摩托车业 | 机械制造业 | 五金与金属制品业 | 矿产业 | 钢铁业金属材料业 | 纺织化纤印染服装业 | 皮革皮具鞋帽箱包业 | 玩具及孕婴幼童用品业 | 建筑与装饰业 园林工程业 | 建材业 | 房地产业 | 零售批发业 | 金融证券保险投资业 | 灯饰照明业 | 电子信息业 | 电子信息元器件与材料 | 通信设备与通信服务业 | 互联网产业 | 电气及自动控制业 | 安防产业 | 电器产业 | 钟表与精密仪器业 | 眼镜业 | 黄金珠宝业 | 美容美发业 | 家政等社会服务业 | 文化产业 | 教育产业 | 烟草产业 | 生物工程产业 | 客运与物流业 | 物资回收业 环境保护业 | 贸易业 | 多种行业 |
| 习仲勋说我是“解放牌” 曾宪梓回忆30年爱国人生历程 |
|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2 月 16 日 19 时 57 分 55 秒 来源: 南方都市报网络版 2008-9-8 10:53:37 |
|
|
- [媒体报道] 世界客青聚香江,喜迎中秋贺国庆 23.10.7
- [媒体报道] 梁亮胜交棒,曾宪梓之子当选主席! 22.8.13
- [媒体报道] 曾宪梓之子曾智明当选广东省客联会长 20.12.14
- [媒体报道] 曾智明到梅县参观考察教育工作:点赞家乡发展变化 倾力支持教育事业 20.7.10
- [媒体报道] 曾智明捐610万港币 金利来捐200台消毒机! 20.2.29
- [媒体报道] 曾智明:继承和弘扬父亲永远跟党走的爱国精神 20.1.22
- [媒体报道] 曾宪梓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梅州举行!一生爱国爱港捐逾12亿港币 19.9.21
- [媒体报道] 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逝世:特首哀悼 社会各界缅怀 19.9.21
- [媒体报道] 香港著名企业家曾宪梓雕像在圆明园揭幕 19.5.24
- [媒体报道] 曾宪梓:梅州是我的家乡,我的根在梅州、心在梅州 19.2.24
- [媒体报道] 大手笔!梅州梅县金利来花园动工建设,计划投资 10 亿元 18.12.30
- [媒体报道] 钟光灵一行拜访曾宪梓博士,曾宪梓:我觉得为梅县人增光了! 18.12.25
- [媒体报道] 曾智明梁亮胜率香港客属总会香港梅州总商会考察团来梅考察 18.11.18
- [媒体报道] 曾宪梓之母用坚强来感染孩子 10.11.10
- [媒体报道] 从贫困中奋起——母亲对曾宪梓的影响 10.11.9
- [媒体报道] 新书《走近曾宪梓》在内地推出 10.10.27
- [媒体报道] 曾宪梓:中山一院让我多活了12年 10.10.10
- [媒体报道] 专访黄洁夫曾宪梓钟南山 10.10.9
- [媒体报道] 金利来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09.12.15
- [媒体报道] 人物专访:客家之光——曾宪梓 09.10.11
- [媒体报道] 曾宪梓的母亲蓝优妹 07.9.8
- [媒体报道] 超级富豪背后的客家太太 07.8.28
- [媒体报道] 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的“抠门”与大方 05.11.14
- [媒体报道] “领带大王”的心愿——访金利来(远东)公司创办人曾宪梓 86.5.22
- [创业历程] 九位华商富豪们的成功创业哲学 10.5.19
- [创业历程] 曾宪梓先生的创业历程 09.9.14
- [创业历程] 曾宪梓:"经商就是智慧的自我较量" 09.6.22
- [创业历程] 曾宪梓以6000港元打造“金利来” 09.4.21
- [创业历程] 曾宪梓:创立“男人世界”的爱国商人 08.12.17
- [创业历程] 领带大王曾宪梓 08.11.12
- [创业历程] 曾宪梓谈创业 称34岁前甚至有穷到怕的感觉(图) 08.2.18
- [创业历程] 曾宪梓为男人的世界创名牌──金利来 07.10.23
- [创业历程] 曾宪梓:用勤劳和智慧缔造男人的世界 07.10.9
- [创业历程] 曾宪梓:客家骄子的闪光人生 07.7.5
- [创业历程] 曾宪梓:靠一把剪刀起家的“领带大王” 07.5.21
- [创业历程] 金利来,曾宪梓,创业报国传奇 07.3.31
- [创业历程] 曾宪梓:不靠菩萨靠人脉 07.3.24
- [创业历程] 曾宪梓畅谈“金利来”创业史 07.3.6
- [创业历程] 曾宪梓:“金利来”王国的创始人 06.12.3
- [创业历程] 曾宪梓与他的“金利来” 05.11.1
- [创业历程] 曾宪梓开班授徒教做有钱人 05.10.20
- [发展战略] 曾宪梓辞任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 其子曾智明接任 18.4.28
- [发展战略] 金利来创始人是哪个?投资价值大不大? 17.1.4
- [发展战略] 金利来 男人的世界 10.11.24
- [发展战略] 华裔富豪曾宪梓:走高档化之路 09.7.13
- [发展战略] “金利来领带”的美丽传说 08.2.19
- [发展战略] 对话曾宪梓 07.8.20
- [发展战略] 论曾宪梓的商业经营管理理论 07.6.8
- [发展战略] 曾宪梓请辞人大常委 遗嘱规定子女平分财产(图) 07.4.24
- [发展战略] 曾宪梓:不靠菩萨靠人脉 07.3.24
- [发展战略] “领带大王”金利来曾宪梓 06.7.25
- [发展战略] 第一访谈:访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 05.2.7
- [发展战略] 不断创新 目光向外——访金利来集团执行董事曾智明 04.1.12
- [发展战略] 曾宪梓:生意经里的“道德经” 02.1.22
- [发展战略] 曾宪梓:“诚信是华商成功的根本” 01.9.17
- [发展战略] 访人大常委会委员 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 99.10.25
- [市场营销] 服装行业内需增长 金利来拓展多家分店 12.1.18
- [市场营销] 非专柜卖的“金利来”皮具 99%是假的 09.12.3
- [市场营销] 领带大王——曾宪梓 06.7.12
- [市场营销] 金利来 靠一把剪刀一个人的工厂起家 06.6.6
- [市场营销] 服饰业候选品牌及品牌官:金利来及曾智明 06.5.6
- [市场营销] “金利来”游太空旗帜归来 曾宪梓视为传家宝(图) 05.11.24
- [市场营销] 曾宪梓困处逢生的秘诀 99.10.15
- [人才战略] 曾宪梓首次宣布:三子曾智明接掌金利来(图) 12.2.5
- [人才战略] 名流访谈:曾智明 这个王子很温情 10.10.22
- [人才战略] 曾宪梓:从实际中得来的经验最宝贵 10.4.18
- [人才战略] 续写“金利来”新篇章 10.1.29
- [人才战略] 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的交权启示 09.9.2
- [人才战略] 客商曾智明:自知者智 知人者明 09.8.10
- [人才战略] 金利来少帅曾智明:延续父辈的成功和爱心 08.10.20
- [人才战略] 利来二代掌门曾智明:搅动“男人的世界”(图) 08.9.1
- [人才战略] 曾智明:“我的梦想在金利来” 08.8.30
- [人才战略] 曾智明:金利来世界的成功男人 07.7.26
- [人才战略] 金利来继承人曾智明:财富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志 07.4.11
- [人才战略] 妙用罗活活,盘活“金利来” 05.10.14
- [人才战略] 香港富商曾宪梓有意退休 笑言集团主席只是挂个名 05.7.15
- [人才战略] 曾宪梓:金利来35岁换班 不贪内地上市 03.12.15
- [人才战略] 曾宪梓之子曾智明突围而出 03.10.3
- [发展动态] 金利来服饰集团盈利下跌 上半年已关店30间 16.8.23
- [发展动态-金利来服饰皮鞋皮具] 金利来皮具 12.2.5
- [发展动态-金利来服饰皮鞋皮具] 金利来服饰 12.2.5
- [发展动态-金利来服饰皮鞋皮具] 金利来 男人的世界 10.12.31
- [发展动态-金利来房地产] 广州金利来数码科技大厦 成熟甲级写字楼 采光好 实用高 12.2.5
- [发展动态-金利来房地产] 沈阳中街购物节 金利来商厦五虎添新翼 10.7.13
- [发展动态-金利来房地产] 梅州金利来时尚步行街城市花园动工 06.2.12
- [发展动态-金利来房地产] 广州金利来大厦建成数码网络商务港 04.12.16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向中山一院捐资500万港元 16.2.7
- [慈善捐款] 瞿振元与曾宪梓约定春暖时节中农大相见 10.11.30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在京颁奖 1750名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10.11.26
- [慈善捐款] 浙江大学曾宪梓教学楼落成启用 10.11.9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曾子故里祭宗圣 捐500万重修古建筑 10.9.30
- [慈善捐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专人赴港拜会曾宪梓探讨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走向 10.8.19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心随神舟一起飞 10.4.18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河南获赠中原圣土宝鼎 10.4.18
- [慈善捐款] 曾宪梓表示:支持武汉大学发展是我多年的夙愿 09.12.20
- [慈善捐款]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访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 09.9.14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向拿山中学井冈山实验中学捐赠款物 09.9.9
- [慈善捐款] 曾宪梓透露已患肾病 靠透析治疗来维持生命(图) 09.8.4
- [慈善捐款] 我们非常景仰您——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拜会曾宪梓小记 09.5.25
- [慈善捐款] 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向华侨大学捐资500万港元 09.4.2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曾为西安交大捐500万建宪梓堂 08.10.17
- [慈善捐款] 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京会见并宴请曾宪梓和霍震霆 08.9.28
- [慈善捐款] 曾宪梓为神七升空落泪 拨1500万重奖航天功臣 08.9.26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捐资1亿港元成立体育基金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发展 08.8.28
- [慈善捐款] 赤子之心报效祖国——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爱国情深 08.6.9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含泪捐千万:希望帮助地震灾民度过难关 08.5.14
- [慈善捐款] 30年向内地捐6.8亿 曾宪梓:自己的方式回报祖国 07.12.17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再捐百万资助延安中学 题写座右铭勉师生(图) 07.11.19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捐建助残研究基金 07.11.1
- [慈善捐款] 温哥华中华会馆设宴答谢曾宪梓夫人慷慨资助 07.8.11
- [慈善捐款] 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曾宪梓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赠100万元人民币 07.7.21
- [慈善捐款] 金利来太子爷曾智明:一捐助就宣扬属于别有用心 07.4.11
- [慈善捐款] 我要孩子们每年捐出2000万元 07.3.5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已奖励教师大学生近1.3万人 06.12.27
- [慈善捐款] 著名港商曾宪梓捐资二百万元助徐州贫困乡村学子 06.7.29
- [慈善捐款] 一餐不超10元的曾宪梓 6.7亿捐祖国 06.7.17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简介 05.12.21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资助奖励优秀大学生逾万人次 05.12.21
- [慈善捐款] 大款们为何不向曾宪梓学学? 05.8.20
- [慈善捐款] 罗清泉会见曾智明 感谢“金利来”助学善举 05.7.22
- [慈善捐款] 曾宪梓及属下企业为国家游泳中心捐赠一千万元 05.4.25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实施奖励计划培育英才 04.12.27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捐资奖励内地一千多名大学生 04.12.24
- [慈善捐款] 黄菊会见曾宪梓和获奖航天科技人员 04.12.21
- [慈善捐款] 曾宪梓捐赠1亿港元设基金会 奖励中国航天专才 04.10.26
- [慈善捐款] 曾宪梓表示将把金利来所赚钱全部赠给国家 99.8.10
- [客家事业] 钟光灵张运全率队拜访曾宪梓博士 17.5.17
- [客家事业] 张文广率队拜访曾宪梓博士 16.7.15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博士给河职院志愿者留言 鼓励学生多参与社会活动 10.12.2
- [客家事业] “我一天生活费不能超50元” 10.12.1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博士竖起大拇指 称赞河源“了不起” 10.11.30
- [客家事业] 三明市委书记黄琪玉、市长刘道崎拜会知名人士曾宪梓 10.11.30
- [客家事业] 解读中原人与客家人渊源 奉献中华汉文化精神大餐 10.11.27
- [客家事业] 香港将于下月12月2日至5日举行首届“香港客家文化节” 10.11.1
- [客家事业] 曾宪梓梁亮胜率香港嘉应商会新一届会董回梅 10.10.17
- [客家事业] 朱泽君拜会曾宪梓博士 曾宪梓表态捐100万支持梅州城市绿化建设 10.8.20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回乡考察后表示将继续支持家乡建设 10.8.19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博士接见在沪客家青年的讲话 10.6.24
- [客家事业] 曾宪梓晤上海客家联谊会丘峰会长、庄重总经理一行 10.3.19
- [客家事业] 图文:曾宪梓获“世界客家杰出贡献”荣誉称号 10.1.29
- [客家事业] 香港客家首领汇聚一堂 发出弘扬客家精神倡议书 10.1.29
- [客家事业] 曾智明: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总裁 09.12.10
- [客家事业] 万里他乡长为客 中原故土盼君归 09.10.22
- [客家事业] 曾宪梓与四百多名中大梅州校友“话”乡情 09.10.18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在2009’梅州•世界客商大会开幕式的发言 09.10.14
- [客家事业] 曾智明呼朋引伴共襄盛举 09.10.14
- [客家事业] 曾宪梓:要致力促进客商的交流团结 09.10.12
- [客家事业] 会长访谈:永远爱国爱港爱乡 09.9.28
- [客家事业] 五十集电视剧《客家人》9月8日举行开拍仪式 09.9.9
- [客家事业] 江西省副省长熊盛文在井冈山会见香港知名爱国人士曾宪梓 09.9.8
- [客家事业] 你是家乡人 我会尽量配合 09.8.10
- [客家事业] 梅州市委市政府设宴欢迎曾宪梓 09.7.27
- [客家事业] 我在宪梓先生家吃午饭 09.6.22
- [客家事业] 名誉校长曾宪梓博士报告会情动嘉园师生 09.4.30
- [客家事业] 游子客地念乡亲贺卡千里寄深情 曾宪梓年初一祝赣州 09.1.27
- [客家事业] 世界兴宁同乡第五次恳亲大会举行 09.1.4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先生简介 08.12.22
- [客家事业] 1985:归还祖屋激发侨胞爱乡热情 08.12.2
- [客家事业] 郑钢坚放歌《客家土楼》惊喜世界三千客属 08.11.4
- [客家事业] 曾宪梓:我回家了——访世界客属联谊会荣誉主席曾宪梓 08.10.18
- [客家事业] 特写:西安以盛唐礼仪迎上千名客家代表 08.10.17
- [客家事业] 恳亲大会迎宾式 西安市长向曾宪梓赠金钥匙(图) 08.10.16
- [客家事业] 3000客家人今晚聚西安 08.10.16
- [客家事业] 曾智明蟬聯嘉應商會會長 08.8.5
- [客家事业] 香港知名人士为赣港两地经贸合作积极建言献策 08.6.4
- [客家事业] 香港嘉应商会赴茂名考察商机 07.11.21
- [客家事业] 曾宪梓认为汕头大发展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07.9.22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坦露心声——为家乡贡献智慧和力量 07.9.21
- [客家事业] 庆祝梅州市曾宪梓中学成为全国示范性高中 07.8.24
- [客家事业] 从叶剑英到曾宪梓 07.4.2
- [客家事业] 评估专家考察嘉应学院德育教育基地——曾宪梓博士事迹展览室 06.12.9
- [客家事业] 山东省举行客属联谊会成立庆祝大会暨海外客属侨领齐鲁行活动启动仪式 06.8.31
- [客家事业] 饶曼妮:让更多客家人为山东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6.8.31
- [客家事业] 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等给河源市富源水电站开工庆典发来贺信 05.12.29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博士在同学聚会中畅谈事业、健康、人生,吐露心曲——终生报效祖国是我的人生追求 05.11.11
- [客家事业] 曾宪梓重游母校东山中学留心声——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志气 05.11.9
- [客家事业] 天下客家天府情缘 曾宪梓:爱吃四川蹄花炖汤 05.10.13
- [客家事业] 嘉应学院名誉校长曾宪梓博士回校考察 05.9.15
- [客家事业] 刘日知赴香港拜访梅州乡贤 同叙桑梓情 共商发展计 05.3.24
- [客家事业] 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采访记述 04.11.30
- [客家事业] 赣江源头客家人“祭坛揭鼎”(图) 04.11.20
- [客家事业] 世客会新闻发布会:曾宪梓参加世客会一波三折 04.11.19
- [客家事业] 客家文化寻根: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举行 04.11.18
- [客家事业] 曾宪梓:关注“力行”情谊重 04.11.3
- [客家事业] 曾宪梓的桑梓情:报效祖国志向儿孙代代相传 03.12.9
- [客家事业] 金利来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博士回山东嘉祥祭祖 02.9.7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嘉应学院曾智明教学大楼落成 曾宪梓等出席启动仪式 17.11.15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勉励学生:为实现中国梦奉献自己力量 15.11.9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在梅州捐资逾2亿元 支持家乡建设发展 11.2.23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客家名贤曾宪梓:客家之子以客为根 以中华为念 10.12.3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情系家乡 再次捐资教育 10.4.26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再捐100万支持梅州家乡教育事业 10.4.8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今日睢阳采集圣土 09.12.3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广东梅州曾宪梓中学 09.9.22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在梅州捐资逾亿港元 08.12.22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河源曾宪梓希望小学奠基 五所小学共获百万捐助 07.9.20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香港嘉应商会会长曾智明 乡贤捐助家乡救灾复产 07.7.2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曾宪梓捐资274万元 梅州宪梓中学两项目竣工使用 06.11.9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金利来副主席曾智明捐100万广东梅州重建4小学 05.8.11
- [客家事业-慈善捐款] 捐赠巨资建校育英才——记金利来集团副主席兼行政总裁曾智明 05.8.11
- [社会责任] 中评两会专访:曾智明谈香港的角色 18.2.28
- [社会责任] 曾宪梓:我跟祖国血肉相连(图) 15.10.9
- [社会责任] 我校马有恒、霍震寰、曾智明三位校董担任亚运火炬手 10.11.22
- [社会责任]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宪梓坐轮椅赶来拜祖 10.4.17
- [社会责任] 曾智明獲獎感開心 08.12.11
- [社会责任] 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换届选举 曾智明当选会长 08.11.28
- [社会责任] 访香港年龄最大的火炬手、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 08.5.4
- [社会责任] 东亚银行总裁次子33岁入选政协委员 08.1.28
- [社会责任] 曾宪梓:情系原乡 07.5.1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发愤图强,回报祖国—参加人民大会堂曾宪梓基金会颁奖大会有感 10.10.2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振川会见曾宪梓博士 10.9.2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吃饭也“打包” 10.8.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曾宪梓-燃情岁月心系广交会 10.6.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客属代表曾宪梓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10.4.1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两万炎黄子孙新郑祭轩辕 10.4.1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一颗可贵的中国心 10.4.1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新浪河南独家专访曾宪梓 10.4.1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10.4.1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郭庚茂会见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10.4.1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丘进校长拜访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先生 10.3.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中国60年变化3天3夜讲不完 外国很羡慕中国 09.10.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专访曾宪梓:没有国家的培育 我还在乡下种田(图) 09.9.23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博士井冈行 09.9.10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花天酒地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09.8.2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周强与曾宪梓会晤交流意见 09.5.2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红色资本家曾宪梓报国有门 09.4.2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两岸共求和平谋发展 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09.1.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称中国经济实力15年后将超过日本 08.12.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中国经济实力过三十年可超美国(图) 08.12.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神七"让香港人骄傲 08.9.2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习仲勋说我是“解放牌” 曾宪梓回忆30年爱国人生历程 08.9.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奖励奥运冠军 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捐1亿港元 08.8.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赞叹中国军事:国人从此不被欺负了! 08.8.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大爱无疆图展”震撼香港 曾宪梓50万购名画 08.6.1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金利来董事局主席曾宪梓:中国一定能办好奥运会(图) 08.6.1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坐轮椅也要传递火炬:要到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 08.5.3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批评李柱铭死性不改 没有中国血性 07.10.2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旗帜鲜明的爱国商人 07.10.2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一生爱唱两首歌 07.7.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我的中国心 07.7.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重要关头就站出来与反对派做斗争 07.6.27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现在是香港最好的时期 07.6.2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领带大王”曾宪梓:祖国越发展 香港越美好 07.6.1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高端访谈:曾宪梓 07.6.1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人心的回归是最大的回归 07.6.7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红色资本家”曾宪梓:香港发达靠内地 07.6.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谈香港回归:脱离实际谈普选对港无好处 07.6.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因年事已高患肾衰竭 曾宪梓公开请辞人大常委 07.4.24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请辞人大常委 遗嘱规定子女平分财产(图) 07.4.24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已请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07.4.2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赵乐际袁纯清会见曾宪梓 07.4.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人大常委曾宪梓:年轻人求职的眼光不妨长远些 07.3.1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回首走过的路 不枉此生 07.3.8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将为国为港做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一刻 07.3.4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专访曾宪梓: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图) 07.3.3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访谈: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图) 07.2.1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徐光春在香港会见了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07.1.20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我教儿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6.10.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唐英年、曾宪梓等香港政商要人确定参加徽商大会 06.5.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贾庆林感谢曾宪梓对中国航天的支持和关心 06.3.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谈和平统一定会造福两岸同胞 06.1.30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张高丽会见曾宪梓 05.9.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张高丽会见曾宪梓 05.9.2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八名受捐学生香港喜见曾宪梓 05.8.2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宴请寒门学子——曾宪梓“打包”记 05.8.22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评价董建华辞职:香港不会因此而震荡 05.3.1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04.10.27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为祖国发展不遗余力--访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 04.10.2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勉励学生:穷困并不可怕 回报祖国是动力 04.5.23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社会未达共识 普选言之尚早 04.4.16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直指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不是爱国者 04.2.14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此生惟愿国昌盛——曾宪梓博士访谈录 03.12.1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代表寄语:首先要教学生学会做人 03.3.1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要做一个编外的党员回报祖国 02.11.11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曾宪梓赠语浙大学子:“勤俭诚信+智慧=成功” 02.4.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始终是两岸桥梁--访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曾宪梓 01.9.19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两会代表曾宪梓京城诉心迹 99.3.15
- [社会责任-全国人大常委] 光辉前程我们共同创造 98.7.31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嫁入豪门:性感女明星能忍是关键 08.12.16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传黎瑞恩意外小产 丈夫曾智明以笑回应(附图) 07.9.20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黎瑞恩前日诞下麟儿 为曾家凑成一个“好”字 05.6.10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黎瑞恩昨日嫁入豪门全面退出娱乐圈 02.12.19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黎瑞恩月中举行婚礼成为曾宪梓儿媳 02.12.6
- [曾智明迎娶歌星黎瑞恩] 黎瑞恩扶未来公公曾宪梓欢喜在心 01.10.15
- >> 返回 [基本资料]